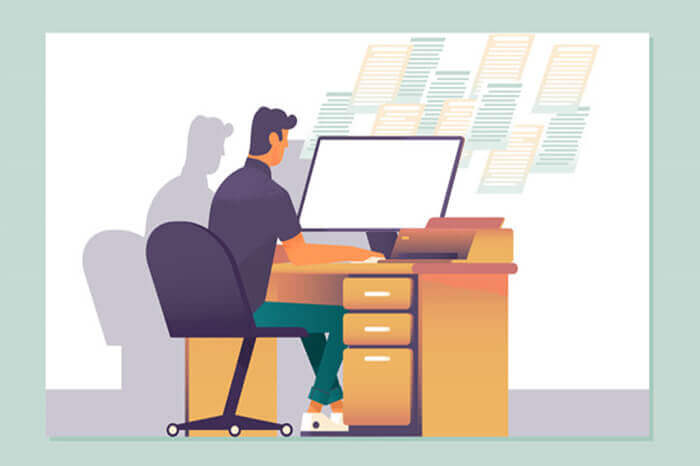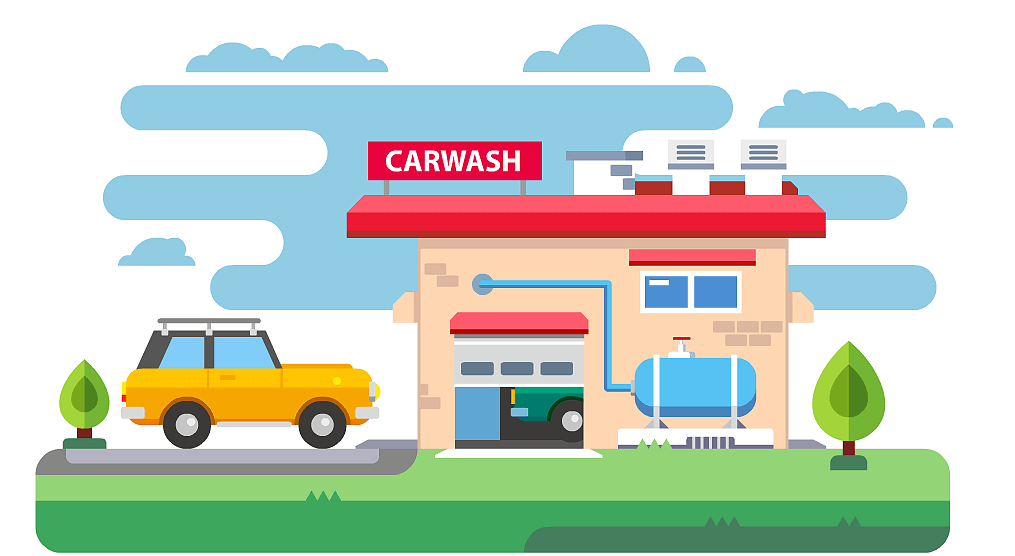魔都寻常
上海真是够魔幻,高耸入云的大厦,恍如巨人般俯瞰着城市,将一切压在了脚下,连渺小的我也一并笼罩。东方明珠塔如一支巨笔,直刺青天;金茂大厦则尖利如锥,似乎要戳破苍穹。它们排着队,静默地立着,却仿佛在无声地喧哗:“看呀!看呀!这便是魔都了!”
可是,魔都的魔力,却未必全在魔幻处,反在那些寻常巷陌间。
清晨的城市里,尚未醒透的街道上,行人稀少,只有早起的环卫工人,正用扫帚沙沙地清扫着昨夜的碎屑。弄堂里,却早早地蒸腾起了烟火气。油锅里的生煎包,在呲呲作响的油花里翻着跟头,焦香裹着油香,四处弥漫;炉火上的粢饭团,被裹得紧实而圆滚,白气氤氲着,蒸腾着;小馄饨在滚水里上下翻滚,汤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人们排着队,安静地等待着。小贩们轻快娴熟地忙碌着,动作利落,不多言语。排队的食客们,彼此目光也并不相碰,各自守着自己的一方空间,却偏偏在这沉默中,透出一种默契的安稳来。
待到了中午,阳光强烈起来,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出刺眼的光芒。我挤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,挤进地铁车厢中去。车厢中的人紧贴着人,各种气味与呼吸混在一处,几乎令人窒息。身边人衣服摩擦着我的手臂,后背抵着别人的前胸。车子开动了,摇摇晃晃,车厢里的人随着车身晃动,彼此碰撞,各自又迅速分开,仿佛有磁石在暗中操控一般。人虽多,却静得出奇,只听见列车在轨道上轰隆隆地行驶。人们低头看着手机屏幕,偶尔有人疲惫地合上眼睛,却始终紧紧抓着扶手,仿佛在喧嚣中紧紧攥住了自己那一点空间与安宁。
暮色笼罩了城市,霓虹灯开始闪烁,像是城市的眼睛纷纷睁开了。我走过一条老街,路边有位老太太坐在小凳上,面前摆着几只竹编的小篮子,里面盛满了串好的白兰花。花儿洁白如玉,香气淡雅悠长。老太太头发花白,戴着老花镜,安静地坐着。霓虹灯光映在她脸上,明明暗暗地跳跃,却并未惊扰她脸上的安详。我买了一串,老太太小心地递给我,花茎上的绿色棉线还带着她指尖的温度。花香幽幽,竟暂时压倒了城市里那些浮华的气息,仿佛在喧嚣里给我辟出了一块小小的清静。
夜深了,高楼的灯光依然明亮,如同城市亮着的眼睛,始终不肯睡去。我缓缓踱步,手握着那串小小的白兰花,香气随着夜风时浓时淡,钻入鼻中。花虽小,香气却清幽,一点点沁入心脾,仿佛有灵性似的,一直抚慰着我。
魔都的魔力,不在于魔幻奇景,却在于这平凡之“常”中:油锅里翻腾的焦香,人海中沉默的坚持,老妪篮中玉兰的清芬——正是这些细碎而坚韧的寻常烟火,默默滋养了这庞大城市的每一寸肌理。
魔都之所以为魔都,不在于高耸入云,而在于它容纳了千千万万人间的呼吸与体温,在喧哗之中,亦保有着一份体面的、韧性的安静。